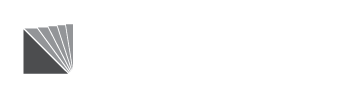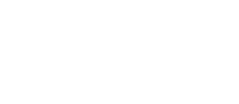逆流而前的思想者
文/鄧伯宸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Camilo Jose Cela),在一項訪問中談到「小說的死亡」這個問題,他認為小說不但沒有死亡,甚至是正在誕生過程中的文學類。他說:「我們寫小說的往往太教條,只承認我們認為可以叫做小說的作品⋯⋯我們為什麼要堅持為小說樹立熟悉的界限或其他呢?完全沒有道理⋯⋯我們不可能完全知道小說一定會是什麼模樣。」
塞拉對小說的看法,很可以將之移植到另一種非文學的藝術領域——繪畫上來。在台灣,現在正有一股越來越強烈的趨勢,亦即本土意識以主流的姿態否定其他的,非我族類的創作理念。本土主義的勃興當然是有跡可尋的。基本上,它延續了七十年代的鄉土運動,是對過去西方藝術思潮主導台灣創作方向的一種反彈。不可否認的,歐美不斷湧入的美術流派觀念,雖曾帶給台灣畫家新的創作刺激,但卻也構生了流行而武斷的公式,嚴重的干擾了美術創作者與自己生活的土地之間互動。從鄉土運動到今天新興的本土意識,無疑有助於打破這種西潮的迷思,並尋回失落的自我,但很不幸的是,任何觀念一旦成為主流(或者僅是自以為是主流而已),便產生了極端的排他性。本土主義成為今天的顯學,在反完全西化的武斷獲得成功後,本身又很諷刺的形成了另一種流行的公式,而派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最嚴重的莫過於無理的排斥不合狹窄本土眼光但仍具優異品質的創作。
我們不否認,藝術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整體社會生活是藝術風格轉變的原動力,而所謂整體生活則是經濟體制、政治模式、社會結構及文化哲學諸多因素的結合。整體社會生活的改變必然導致鑑賞中心的改變,對藝術家具有無法估量的壓力,乃不得不隨著新的鑑賞中心而旋轉。八十年代的台灣正是處在一個急遽改變的風暴中,尤其是近兩年來,在經濟奇蹟的支撐下尋回民族的尊嚴後,政治、社會、文化的大幅轉型相繼發生,且於有意無意間向回歸本土幅湊集中,駸駸然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藝術家身為社會的一份子,且總是以感受性走在時代前端者自居,其隨著此一風潮而升浮,實是無可厚非的。
但值得警惕的是,在傳播資訊泛濫及文化產品商業化的今天,任何藝術風潮一旦形成,便很容易墜入市場性的流行陷阱,而以一套獨斷而專橫的規則框住了鑑賞的眼光和心靈。以致偏離了藝術的真精神。康德在其「美感判斷之批判」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沒有目的之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他所謂的「目的性」是指個人在其創造本身和創造結構中表現的一個統一形式,而「目的」則是指外在於個人創造的決定因素,「沒有目的之目的性」即是說在自己本身之中有自主重心的創造活動。藝術家的自主重心應該是與整體社會生活互動的,並存不悖的。但是,先受整體社會生活的牽引而失去了自主重心,「沒有目的之目的性」,就變成了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T.W. Adorno)與奧霍克海默(M. Horkheimer)批判當代大眾文化的「為了目的之無目的性」(Purposelessness for purpose)。這裏所說的「目的」是文化市場所決定的目的,而「無目的性」則是說沒有內在自主的創造性。對台灣今天方興未艾的本土意識,我們所擔心的,正是這種文化市場、傅播媒體所形成的強勢外在決定因素會扼殺了美術創作者內在自主的創造性。因為在這種情勢下,藝術家可能變成諂媚的,投市場所好的,為支持流行思潮而提供滿足傳播媒體口味的設計。如此一來,藝術成為客觀環境的反射,再也不能從有機的社會整體中抽出任何靈感或力量,藝術患了貧血症,只不過徒然擴大了市場無所不在的影響力而已。
當我們翻閱國內僅有的兩本美術雜誌「藝術家」和「雄獅」時,映入眼簾的那些畫展廣告,多是台灣第一代畫家或大陸畫家的作品,蟠踞著印刷精美的大部分篇幅,要不然就是隨風走雨的「現代水墨」,以強烈裝飾性的淋漓分擠一席之地。商品文化的廣告與當代藝術主流的結合,正顯示出市場導向的藝術樣貌已是今天文化最突顯的表徵,至於其內在則是精美包裝的填充物。「無目的性」的思想和觀念,究其實際只是借用的思想和觀念,只能產生低水平的藝術,當藝術家與社會有這種關係時,便註定了必將日趨衰落。
藝術家反抗如此的衰落可以有兩條路,一是絕然的切斷與社會的關連,成為一個革命的藝術家,亦即自覺的用他自己的藝術來改良社會的情勢。但這種藝術家是少有的。另一種情形則是藝術家對其所處的社會產生一種心理狀態,他的心跳與社會意識一同搏動,但他卻不妥協於現存的美學價值,而追求他自己的美學價值。這種藝術家往往是孤獨的,他們不像革命的藝術家猶能以驚世駭俗的大逆不道招引追隨者,他們總是默默的在實驗室中進行實驗,而在實驗的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客觀的現實,而是「真正的困難在於證明一個人的信念」(塞尚語)。因此,他們正如塞尚在二十世紀初所說的:「於是,我將繼續研究⋯⋯。」
「南台灣.新風格畫會」,在台灣今天這種「有目的之無目的性」的藝術氛圍中,正是一個相當典型實驗者。他們極力的與當前的藝術市場及媒體保持距離,而為了共同的理念結合成一個孤立都不孤獨的組合。葉竹盛、楊文霓、陳榮發、曾英棟、黃宏德和顏頂生,四年前即跨出了對藝術環境惡質化不妥協的第一步。在一篇宣言式的文件中強烈批判藝術工作者「忽略了觀念、思想、感覺、實驗、冒險之精神,一味做形式、色彩的奴隸。」
值得注意的是,從他們強調思想、觀念、感覺、實驗及冒險的立場來看,「南台灣,新風格」對藝術的基本態度是向西方現代藝術的發展認同的。換句話說,他們這一批從三十歲到四十歲出頭的年輕藝術家,身處在台灣資本主義邁向顛峰的發展過程中,親身體驗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之痛,在科技抬頭,經濟繁榮,都市化程度加深的刺激下,眼看著環境污染,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之間的乖離不斷惡化,在心靈上遂不可避免的經歷著西方現代藝術前輩們所走過的心路歷程,再加上他們原本即在教育上深受西方現代藝術的薰染,於是更加強了他們現代藝術的精神武裝,而樹立起一面不苟同於台灣藝術環境的大纛。他們反對形式的形式化,他們杯葛色彩的專斷性,他們將觀念、思想、感覺視為藝術的表現主體,把實驗、冒險做為呼應這個劇變時代的手段。觀察他們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們毫不猶豫的拋開了各自具有的深厚寫實基礎,以及絕對有能力做到的形象變形,而採取抽象的策略,亦即主觀主義的創作理念,以突顯觀念、思想、感覺在作品中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他們大量的選用非傳統性的素材,打破繪畫資源的局限性,設計、製造新的效果以表達他們主觀認知對客觀環境的反應,充分顯示出他們的實驗的精神。
楊文霓最近表示,她正在對一種新的材料進行試驗,希望能有所突破。事實上,她不止試驗材料,還要試驗溫度,企圖將她主觀的意念完美的移植到火與土的相容性上,並為陶藝打開新的路向。葉竹盛的素材中也包括泥土——陶土、紅土,但都是將它們轉化成顏料。他緊緊的將心靈黏附於選用的材質,從它們的屬性中去尋找創作的靈感,為此,他甚至對素材產生一種感情。陳榮發在巨幅的未完戍作品前,腳前堆滿了各類的顏料,感覺與思想俱陷入「入定」的狀態,醞釀畫面的呈現,並使之符合他與現實互動所產生的內在意念。曾英棟在啟聰學校教畫,畫面上揚溢著無聲世界的內心呼喊,強烈而直接的視覺效果,多! 素材的運用,營造出作者與現實問若即若離的聯繫。黃宏德的構圖看似最簡單,但他的內心都最騷動,素雅、簡潔的平面中,自然而隨緣的筆意,透露出精神上企望廣濶空間的衝動。顏頂生呈現一種東方式韻味,簡單的線條以蔓延的方式或糾結,或遙相呼應,在晝面上拉出遼濶的視野,而浮現寧靜的恬淡。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說明、描寫,或詮釋這六位畫家的任何一件作品。意境是畫家自造的,或者說作品是感受的投射。重要的是他們創作的動機和理念,以及隱藏在動機和理念背後的一些主客觀因素。他們既要對現實的「無目的性」有所回應,先天上做為一個中國人又必然有一種內爍的東方性的衝動,因此在藝術的表現上基本上會經過矛盾產生,綜合、化解、統一的過程。他們注意到「觀眾、藝術家與時代疏離感」的存在,極欲打破(或者至少不願被捲入)這種逆向的潮流,而向西方現代藝術的精神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又「企圖以新的形式表達比較中國的氣質」(葉竹盛語),於是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思索的時間,拉長了創作的過程,其目的無非在「求變」、「求新」。這種有別於傳統藝術怡情養性或現代社會功利主義的態度,必然會使他們的作品中包含了更多的語彙,而這些語彙對一般人——包括藝術家及非藝術家——卻是陌生的。這正是為什麼「南台灣,新風格」近幾年來受到某些人批評的原因。有人說,「他們所講的,所表現的,只有他們自己瞭解而已。
問題就出在這種藝術家與現實之間無法聯繫的距離上。「人們不和我們在一起。」克利(Paul Klee)如此大聲疾呼。但是,這種孤立並不是藝術家的錯。事實上,「南台灣,新風格」在精神上也許比一般人更趨向於去瞭解現實,他們對整體社會生活的改變有著更強烈的感知,他們對傳統不但不刻意的去反對,甚至積極的從傳統中去吸取可用的養份。如果一定要把這種孤立說個明白,只好將之歸疚於「南台灣,新風格」的藝術家們都太愛「思想」了。
楊文霓反對美的欣賞是直覺的,她強調美的傳達常出之以借用的、隱喻的方式。陳榮發作畫時,動腦的時間比動手的時間要多得多。葉竹盛強調創作的過程,從肯定到否定,目的根本不存在。所有這些態度都與今天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念不符,他們追求的正是康德的「沒有目的之目的性」。創作,對他們來說只是有內心自主重心的創造活動而已,不幸的是,今天台灣大眾化的文化市場是不接受這種藝術品的。
威廉·泛林吉(Wilheim Worringer)說:「反形象的藝術,一定是大眾所不接受的。」而就藝術的本質來說,思想性越強的創作,其反形象的程度便越大。「南台灣,新風格」對現實的反動正走上這樣一條宿命的道路,此即藝術的哲學化與現代社會泛目的化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化解的。但是,我們在本文的一開頭就引述了塞拉對小說形式的觀點:「我們不可能完全知道小說一定會是什麼模樣。」對於藝術或繪畫,我們也堅持這一看法。藝術會變成什麼模樣?「南台灣,新風格」的實驗和冒險絕對值得肯定,但是實驗和冒險也是有風險的,做為一個真正的現代藝術,是必須要有這種心理準備的。
資料來源:展覽畫冊。選錄自鄧伯宸,〈逆流而前的思想者〉,《1990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