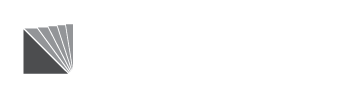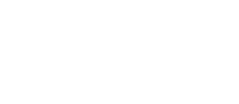訪談實錄——洪根深
日期:2020年8月7日
地點: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受訪者:洪根深(藝術家)
訪談人:蔣伯欣
蔣伯欣 (以下簡稱「蔣」)
洪根深 (以下簡稱「洪」)
蔣:有關於從現代水墨到複合媒材的使用,以及您後來提到的後現代水墨。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加入水墨之外的媒材?在您的作品中您自己是如何區分水墨和複合媒材作品?怎麼看待「後現代水墨」這個詞?
洪:我早期從傳統水墨開始。因為1960年代我接觸到的都是體制內的雜誌,所以小時候所臨摹的大部分都是渡海三家的傳統水墨,就對水墨畫這塊有一個基礎在,那麼到了大學以後就選擇了水墨這條路。在那個年代我們會依稀聽到東方跟五月的運動,我大學的時候很嚮往像劉國松、莊喆或其他東方的藝術家和他們的思想,以及野人咖啡屋、天琴咖啡屋、文星書店和峨嵋街那邊一些文人雅士的聚會和氛圍。這樣的藝術創作的感覺是我們在澎湖或南部沒有的。聽到有關劉國松代表的五月,他們對傳統繪畫體制的抗衡,也閱讀了《文星》雜誌裡面很多作品的介紹,加上我喜歡存在主義,以及我家族對於漢學的基礎,形塑我水墨創作中東方體系的結構。在大三的時候我就開始做一些水墨實驗,在教室走廊辦了兩、三次的觀摩展,也曾經參加一些校外展覽,例如臺北市美展和全省美展。但大學參加這兩次美展後就都不參加了,因為我想走自己的風格,所以慢慢的我有更多風格的呈現。畢業之後的風格是從在澎湖開始的拓印技巧產生,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就是既然傳統水墨的皴法是筆觸,那是藝術家面對當地的風土人情跟自然景觀的紋路所展現出來的20幾種的皴法,那如果我今天面對臺灣的山川,我應該用什麼樣的皴法才能表達這塊土地的面貌?1970-72年這段時間我在澎湖當兵和教書,我就在想怎麼用實驗性的技法,去探討故鄉澎湖的硓?石風貌。忽然之間有一個塑膠布的拓印(的想法),利用它墨刷過去的時候產生的內聚力,拓印了之後污跡的點,有點符合我想要的那種千瘡百孔的硓?石(房子)的樣子。所以從1973到1976年我在雄中的時期,幾乎都是藝評所稱的「枯山水時期」,也就是用塑膠布拓印的技巧處理現代水墨。那時候我也與朱沉冬和羅門有一些交往,他們也一直鼓勵我走現代水墨這條路。1977-79年,水印技巧是我在拓印系列之後想實驗的技巧。中國的畫論裡有水畫和火畫。通常我們在寫毛筆字的時候都會沾水,但我們不去注意這個動作就會疏忽掉,有一次我在寫毛筆字,忽然之間我看到了墨的浮現,覺得很漂亮想說是不是能拿來拓印,所以拿了宣紙來試試,結果那個流墨好像星球一樣,我想這是不是畫論裡所講的水畫的問題,墨和水的比重呈現的現象。1977-79這三年我一直在做水印和拓印的技巧,有一天我在雄中的圖書館,翻開報紙一看,《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裡有一張劉國松的作品,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一張水印的作品。那個時候我心裡愣了一下,想說我做好的作品要不要發表,別人看來會不會認為我是抄襲劉國松的,所以我焦慮了一個禮拜,後來決定發表。因為劉國松在香港,我在臺灣,兩個人在不同的地方所做的水墨技巧實驗雖然不謀而合,但是做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水印之外我加入很多比較具象的東西,並以噴漆、剝落的方法來處理畫面風格,所以當時毅然而然在楊興生的龍門畫廊兩次發表。兩次發表之後,水印技巧既然已經太普遍了,我就轉到對人物的思考。
大約1979年,那個年代也是所謂的「鄉土主義運動」,我就在想,傳統水墨的源頭、中國最早的水墨繪畫應該是人物。民國六十年代的鄉土主義運動的時候,很多人畫農村、頹壁、牛車等等,我認為那是一條面對鄉土的結合,我不希望自己走那條路。還有社會事件和民族意識的路。但反觀當時的人物繪畫,李奇茂等人所畫的作品或多是直接移植過來的邊疆采風,看不出生活在臺灣的藝術家所描繪的土地風貌和人物,晚期後有「夜市」、「小市民」等風土人情。所以我想要擺脫山水來表達土地和人性的問題。我從素描的基本開始,把中國的線條拉進去,把反光面、留白,還有人物的分面等素描的方法融進人物的表達。我又想,水墨的人物大都是畫高士等上層階級,可是臺灣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是靠藍領階級的打拼才建立起來的奇蹟,我想用我最親近人群來表達臺灣文化精神,所以我開始描寫比較藍領階級的人物,比方說畫斑馬線的、跟垃圾車的勞工階級。1979-80年這段關於人物的作品,前後大約有30-40張,在美國新聞處和高雄都有展過,被認為有臺灣的味道。1981年的時候我又開始想,不畫那麼寫實的人物了,就有一些勾勒的人物加上水印的技巧作為背景(的作品)。
洪根深,《觀》,壓克力顏料、墨、宣紙,44X68公分,1981年
蔣:像《觀》這件作品。
洪:對,那只是一年而已。那1980-81年有段時間宋楚瑜當新聞局長的時候,已經有點快要開放的氛圍,我們曾經跟臺灣的文學家像臺中的楊逵、高雄葉石濤等一起遊覽,參觀中船、十大建設、臺南的北門等,回來後我就畫了4張作品,現在都捐出去了。有一張是火畫,那個時候我畫的很完整,但覺得還不夠,它必須有一些穿透,所以畫完後整個用菸去燒燙,所以這是80年代人物創作的一張,一共有四張。
蔣:都是叫《汗與熱的交織》嗎?
洪:不是,《藝術泥爪》裡有鄭穗影的藝評提到這四件作品。
洪根深,《汗與熱的交織》,壓克力顏料、墨、宣紙,150X268公分,1981
蔣:您可以多談一下您和文學界的接觸嗎?
洪:我剛來高雄的時候先認識朱沉冬。他當時在救國團和高雄女中課外文學指導,跟莊喆、于還素都很熟,早期跟海軍的孫瑛、馮鍾睿等四海畫會成員也都熟。我剛來高雄在臺灣新聞報社辦了一次個展後認識了朱沉冬、李朝進、陳瑞福和薛清茂。從此我跟朱沉冬就合得來。因為朱沉冬是詩人,也畫抽象油彩,所以他跟我介紹了羅門、蓉子、張默、羊令野、于還素、張拓蕪等現代文學的作家。像張默、羊令野、于還素都曾經在《中華文藝》、《創世紀》等報章雜誌上評論我的作品,所以北部的現代文學界跟我也都有接觸。可以大膽的說高雄這邊的畫界我跟文學領域蠻有關聯。因為我畫了一些鄉土(的主題),跟葉石濤結緣。那個時候有一些鄉土的文學家在報社裡面當副刊主編,像許振江、莊金國、曾貴海、鄭烱明、陳坤崙、莊金國、黃樹根都有來往。還有楊青矗,我幫他畫過很多書本封面設計。《文學界》第一次開會的時候邀請我,他們創刊第一年的四期就用我的作品當封面,裡面有兩張已經賣出去,另兩張捐給高美館。前幾年鄭炯明來找我,想成立文學聚會的場所,要畫一些文學家肖像放在館裡面,包括臺北的李敏勇。鄭炯明、陳坤崙、葉石濤、鍾理和都畫過像。我跟鍾肇政也有緣識,《民眾日報》在高雄辦報的時候。所以在南部這裡和1970-80年代臺北現代文學界和1980-90年代高雄的鄉土文學家都有互動。
蔣:剛剛您提到這些現代詩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跟左營軍港有關,像瘂弦等,是不是說這個地方的特質去孕育出一種海洋性的,或者說從軍港出發產生出的現代性,不知道您怎麼看這樣子的詩跟畫之間的交流關係?還是說他們各自為政?
洪:朱沉冬以前在臺北,所以他跟那邊的文學界,現代藝術運動多少都有接觸。這邊的四海畫會是海軍的,這個關係我不太清楚,但可以說在那個年代,朱沉冬擁有救國團的資源,他充分利用在文學的推廣,救國團的寫生隊,和他私底下的文學班。這裡面牽涉到一些現代詩、現代文學。另外他是《臺灣新聞報》的副刊「樂府藝苑」主編,他每一到兩週都有一篇評論。那個時候我跟朱沉冬、葉竹盛我們三個人組心象畫會,還想著要有本雜誌,可是其實朱沉冬在高雄已經有結合孫瑛、馮鍾睿、白浪萍。臺北來的藝術家、文學家多由白浪萍招待,羊令野有一次來的時候在白浪萍家裡當場揮毫,我家裡有一些羊令野和于還素的書法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寫的。所以那個時候有所謂的雅集,音樂家陳主税、臺南的林榮德、李朝進、我還有朱沉冬、魏端等這些人都有聚會,奠定一個詩和畫之間的交錯,在1970年代的高雄蔚成風氣。包括葉竹盛,他後來去西班牙,包括蘇瑞鵬、劉鐘珣、黃明韶都有接觸,這裡面形成高雄當時詩、書、畫、音樂、建築整個藝文界燃燒生命的氛圍。可惜留下記錄不多。1972年白浪萍、朱沉冬、陳主税、林榮德他們有出一本《藝術季刊》雜誌。[1]
蔣:後來又出了《山水詩刊》(1976年)。這個團體在1970年代高雄算是蠻特別的。
洪:對,因為它結合了很多元的元素。而且傳統繪畫進不去。像羅清雲雖然接觸也多,印象中還沒或是我記錯了⋯⋯現代畫展有參加。
蔣:同一個時代在高雄藝術界中是不是還是有一些不同圈子的狀態?像另外一支所謂本省籍的像劉啟祥他們,南部展、高雄美術研究會。我有幾個問題跟這個有關,比方說後來在1972年左右林有涔他們另外創了高雄市美術協會,跟「高雄美術研究會」就好像有點分家了的味道,您知道當時這樣子的原因在哪裡嗎?
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們這兩個會的成員最早都是一起的,包括嘉義、臺南那邊。可能是有一些人意見不合。
蔣:像原本嘉義、臺南和高雄是整個串連的,但是後來郭柏川臺南這邊就退出了,為什麼他後來離開沒有跟劉啟祥這邊再繼續合作?
洪:劉啟祥是從新營過來的望族,臺灣那時候能去留學的不多。那個年代高雄的畫廊最早是劉啟祥南部展那時候有一個,黃冬富去年寫過一篇,但應該也不會寫到他們之間氛圍的變化。我只了解到, 林有涔離開後跟劉清榮、宋世雄他們幾個自己立案。南部展那時候沒有立案,可是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推出的展覽方向和策略對於高雄的美術運動有多方面的助益。比方說它有徵畫,間接提攜新人,我和黃光男都有參加他們的徵畫比賽。黃光男參加過南部展成為會員。李春祈也是。我那年也是通過徵畫首獎,成為會友一年然後他們邀請我入會成為會員。我那時候就在考慮不參加,因為我的屬性不一樣,我將來想要處理自己的風格,所以就沒有正式參與畫會,但是我跟他們畫會還是有很多互動。反而我跟林有涔這邊的互動比較少。以我個人來看,南部展的層次、風格、精神狀態比較清楚,高雄市美術協會在1970年代跟南部展比較的話風向與質感略有不同。至於以後他們的發展狀態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蔣:我問這問題跟您的創作風格有點關係。現在史家來看他們會把劉啟祥、張啟華這一支稱為「白派」,跟後來您發展出來,倪再沁、鄭水萍他們所說的「黑派」,好像在高雄變成有兩個不同的面貌。例如在講白派的時候就會講到高雄的光和熱,算不算一種士紳階級所發展出來的善用白色的風格?因為您也寫過美術史,您怎麼看這個角度?
洪:那個白派、黑派是鄭水萍文章裡提到的,他是否引用美術家講陽光、明度和色彩關係,把南部展的風格列入到白派。南部展早期絕對有師承,因為沒有學院,所謂師承是劉啟祥的畫室還有比如說陳瑞福的畫室,或者是詹浮雲的畫室。這種師承的道統和風格一直維持,別人看來比較屬於印象派的風格。鄭水萍怎麼論白派和黑派的關係,如何把我論為黑派的關鍵人物來講,以我本身觀察,認為劉啟祥這派是白派的觀點主要是從色彩跟內涵風格比較唯美的塊面出發。至於在1990年代後,高雄發展出來的所謂的「黑派」,比如說鄭水萍、李俊賢、倪再沁、陳水財的論述,都會牽涉到土地的問題。1970年代後,重工業在高雄快速成長,大卡車、躁鬱的感覺、空氣污染等,使人的心性無法調適,產生出創作裡焦灼、黏性跟幽深的感覺,呈現出不同於南部展優美柔性、陽光浪漫的風格面向。也就是說同樣在那個年代,南部展或高雄市美術協會等其他畫會,他們在創作時是用過往的師承技巧跟自己所接觸到的眼光去描述他所看到的土地和結構。現代藝術家雖然也承受一些學院的表現,可是回到這個地方後,有能力去反省和判斷他要畫的風格是不是符合這塊土地的面貌和圖像。如果反省過後,他還是回到原來的學院派的東西,就還是沈澱在白派這一塊,如果他能有自己的衍演和眼界轉化成他自己有成熟度的技巧,重新出發再詮釋當下的土地和環境,也許他就會回歸到黑派這塊。這兩塊黑與白我認為是每一個人用不同的眼光去面對土地文化。2004年我在屏東開畫展,因為在屏東我想請莊世和來寫我的論述,莊世和這個人很有趣,很直接,他說洪老師你的畫很黑,可是我看到臺灣的社會沒有這麼黑,我不能寫你的作品。所以他們的年代跟我的年代,他們的思維跟我的思維是不一樣的。在創作當代水墨或後現代水墨的時候,我們都對傳統繪畫保留一種尊重,如果沒有傳統繪畫絕對沒有辦法翻新到當代或後現代水墨這塊,而且歷史文化的資源就是後現代水墨創作翻新耕耘的素材,所以白派或黑派也好,都應該共同存在。
蔣:這也涉及到您的風格轉換,如何觀察您藝術創作和臺灣環境的關係?1979年在高雄是一個關鍵轉折,我也想跟老師請教您當時對12月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有什麼樣的觀察?
洪:高雄多是移民,整個臺灣都是移民社會。朱沉冬是省籍人物,那我對省籍人物完全沒有排斥,因為我的家鄉在澎湖,我家、村莊包括洪家祖祠通通都是軍隊,所以我小時候吃的菜都是辣椒,洪家祖祠都被藝工隊進駐。我那時候接觸到很多藝文界的人,兩位(有)緣人──一位是篆刻的鄧本峨、一位是朱恆耀,所以我小時候就沒有省籍的隔閡,而且講得一口標準的國語。我結婚的時候是在澎湖,有一天林玉山老師來澎湖,我接待他,我說老師我因為教書要去高雄,他介紹我一個人,就是詹浮雲,詹浮雲又介紹朱沉冬,漸漸的我認識很多人。在那個時候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和保釣運動,臺灣民主意識跟土地運動氛圍出來,才會有美麗島事件。臺灣所有的民主運動、農民運動應該都是從南部、中部帶起來的。那一年我在高雄中學教書,那個時候我跟楊青矗已經很熟了,會交換一些想法,那天晚上我從鳳山回來就聽說了,中華路、中山路整個封了,還有拒馬。之前所有的高雄選舉運動就是兩派,那個氛圍已經慢慢出來了,在臺灣的民主運動裡它是必然要發生的,比如說施明德也是雄中的,呂秀蓮在美國時和楊青矗都有通信,他們在民主運動這塊(的想法)我可以感同身受。我在處理水墨的人物的時候就想表達土地裡面有血有肉的東西,之前的現代水墨風格也不足以表達我對土地文化的關注,用山水表達的型態,跟我直接用人物來表達是不一樣的,悠然見南山那種感覺已經不適合表達生活在臺灣那個年代的人對政治社會關注的問題。
蔣:曾有論者指出,您曾在1980年代初期受英國畫家培根的風格影響,可否請您談一下,是在什麼機緣下接觸了培根?您如何看他的人物型態表現與場景安排,怎麼運用在您的創作上?
洪:人物畫之後我還覺得不能滿足。我在大學有接觸培根和亨利. 摩爾等。亨利. 摩爾作品有一些瘦瘦的、好像被空氣壓縮的人物,還有一些破碎的、黑白灰的作品。培根表現的人,好像被拉進屠宰場再出來的那種,人體極端痛苦的扭曲狀態。如果一個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面,面對很多沒有辦法抒發的情況,就好像培根這樣的作品,血肉模糊的,這樣的東西很觸動我,包括亨利. 摩爾的人物那樣,被空氣壓縮拉長的,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所呈現出來的東西。也剛好我想要轉型,有一年的時間我沒辦法創作,因為一直不安,所以用了一些扭曲的、類似立體派的分離的方法湊合起來表達人、夫妻之間、家庭之間沒有辦法共融的現象,後來轉型到「繃帶系列」。在這之前有一張《人性之牆》,已經從人物畫的外表慢慢往內心去做,到「繃帶系列」之後逐漸用形體、符號來呈現。這件《人性之牆》的立足點是一點而已,是一個不安的狀態,不是一個正常的三角錐,是一個倒三角錐的狀態,牆面都是人物堆積,好像被千斤壓頂後再出來的人性之牆。
蔣:在這裡轉向蠻大的,從小人物的光輝轉到人的創傷的一面。
洪:對。早期我閱讀存在主義的書,我們那個時候很流行,我又接受了一些培根的東西,很多東西夾在裡面沒有辦法解套,包括臺灣民主運動、美麗島事件、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等整個臺灣的不安、何去何從的大時代。
蔣:在作品的形式表現上,抽象山水當中用塑膠布去拓印,處理到很多關於面的問題,到了《人性之牆》、《夫妻》還有後面「繃帶系列」,人體跟後面的背景之間有各種不同的線、面切割處理。您怎麼看待後期有了形體之後,形體跟面之間,跟場所或空間之間的關係?
洪:因為現代水墨或實驗性水墨那塊,用純技巧去處理自然景觀的東西,跟處理人性內心空間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捨去了比較傳統的點線面的處理。心裏的空間用手去摸是抓不到的,眼睛也看不到的。如果繪畫只是借用傳統的點線面或色彩表達模擬外界的空間,那必須要通過自己本身的介面去處理這塊。那我在處理人性這塊的時候,要達到那個空間我必須要利用線條的拉扯、推展、壓縮空間透視。
洪根深,《夫妻》,墨、宣紙、壓克力顏料,79X60cm,1983
蔣:所以它是帶有輔助的效果?
洪:對。
蔣:那像《壁畫》這件作品的實線跟虛線之間呢?
洪:沒有什麼差別。主要是面和面之間,想要用立體的、又是半浮雕的方式去做,換句話說有一點3D的想法在裡面,才會有空間的牆面切進去。
洪根深,《壁畫》,墨、宣紙、壓克力顏料,83X61cm,1983
蔣:像《現代‧人性‧生命》這件?
洪:1983年我開始做後現代水墨。這件我在描寫臺灣的史詩。那時候剛好一個朋友戴威利要成立一個畫廊,我鼓勵他走現代這條路,結果他只開了一年半就關門了。第一檔展覽是我,第二檔是「笨鳥藝術群」他們,第三個是攝影的侯聰慧他們。這張作品是開館的時候用三夾板訂了一面大牆,我在上面畫的。那時候李德親自下來看我完成。這件作品已經開始有繃帶人物,是想說臺灣人民渡過黑水溝上岸,然後用結構斜線過渡去到光明的那一面,走過了臺灣整個農業工業運動。這張畫集結之前所有的技巧和實驗性風格,有部分先裱宣紙再畫,畫完再撕掉,有一種滲透的方法(白色長條狀的部分)。這張畫在藝術家雜誌有被評論過,在臺中、臺北都展過。水印、摺紙印、壓克力顏料等技巧都有用。之後都是「繃帶系列」。「繃帶系列」持續了三四年,變成人性符號,所以會一直沿用,偶爾會出現,我今年畫武漢肺炎的時候也出現。
洪根深,《現代‧人性‧生命》,墨、宣紙、壓克力顏料,177.4X1430.4公分,1983
蔣:《黑色情結》是1989年開始?
洪:對,多媒材系列。1987-88是《新傳說》,有一年的時間,剛好是解嚴的時候,臺灣的《新傳說》就是解嚴。1989年後就開始《黑色情結》,我那時要參加一個展覽,鄉土文學的藝術家黃樹根,他曾經在1983年大畫《現代·人性·生命》裡寫過我的序,用詩來寫。他對我鄉土運動、《文學界》封面那時候的作品很清楚,有一次高雄縣政府邀請我跟劉耿一和臺北的藝術家三四個人在高雄縣的國父紀念館開聯展,黃樹根參加座談看到我這樣的作品後提出一個問題,洪根深你以前的畫很有臺灣鄉土的味道,為什麼這次沒有?我說不對,我是轉換到用另外的人物表達方式,處理我面對、所在的高雄都會和人性面,用「黑色情結」這樣的字眼串聯我的話題。這次座談會裡我提出黑色情結,後來鄭水萍、李俊賢會陸續提到黑用來描繪高雄場域我認為是有所關聯。

洪根深,《黑色情結之20》,墨、紙、畫布、壓克力顏料,116.5X91cm,1990
洪根深,《黑色情結之20》,墨、紙、畫布、壓克力顏料,116.5X91cm,1990
蔣:在《黑色情結》中用的多媒材,樹脂、石膏還有在紙上形成一些肌理,好像前一個階段《新傳說》裡也有一點。這種畫風在80年代還滿盛行的,包括新表現主義,您當時有一些接觸嗎?
洪:新表現主義⋯那個時候在臺北的藝術家,留西班牙的,或是高雄的葉竹盛就很明顯會用到一些物質材料,而且是很單純直接的物性的東西。跟我處理這邊的東西不太一樣,我是借用過來,如果用一個當代或後現代字眼來處理是非常容易轉介的。後現代對一個過往的、文化歷史媒介的套用、挪用再轉換是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他就是不確定的、正在進行式的,所以才會有很多論戰。「繃帶系列」那時候完全是紙,1987年《新傳說之1》這張是最早的多媒材。比如說「繃帶系列」是現代水墨,如果我們要從傳統挪用過去,傳統材料不能滿足我,所以我必須要開發和實驗很多材料。新表現主義以及原生藝術很多東西是可以拿來運用,表達自己的創作想像。我也看到楚戈他在畫水墨的時候是用畫布,那我想要很多媒材來表達我的創作,於是想到為什麼石膏不能用,所以這張《新傳說之1》嘗試是石膏或有些加樹脂?忘了!我純粹用黑白的墨、跟人物的線條和刮痕來處理這張作品。這張北美館收藏了。
蔣:滿有代表性的。新表現主義會用這樣的方式處理畫面肌理,有一部分是要回應一些歷史或人類集體記憶的命題,那您的命名「新傳說」是不是也有意去探討歷史或時間性的一些主題?
洪:我就是直接探討、表達臺灣經過這樣一個民主運動在1987年解嚴,解嚴就是一個歷史劃時代,就是一個「新傳說」。高雄現代畫學會也是那時候成立的。
蔣:您在「黑色情結系列」中有很多不同形體的處理,是您自己的隱喻轉化嗎?
洪:對,在那個年代很多無序、漫天的東西爆發出來。那種青黃不接的感覺,我認為到現在還是。臺灣的民主的基點太低,時間也不夠深,很多做法還不足以呈現偉大的民主那種狀態,所以我們看到的很多都是人與人之間、金錢、權力結構之間的拉扯。這段時間我的畫裡面只有這張《霧台遊記》比較沒有講這些社會現象。
洪根深,《新傳說之1》,墨、宣紙、壓克力顏料、石膏、畫布、樹脂,112X145公分,1987
蔣:1990年代後您還是延續這種黑畫的風格。
洪:對,1995年我特地畫了《山水幾何之5》。那是面對臺灣,我把「山水」這個詞對應到國土,就是那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城春草木生的木字,在作品《念土》[2]中改成不字),山水幾何,反過來就是「何幾」,我們的國土在哪裡?我們的山川在哪裡?有一種反問的命題。我的畫裡只有一兩張風花雪月。
蔣:請您談一下1997年《形象》。
洪:這張是處理「二二八」的,我是描寫女性。很多228事件男孩子都往生了,家庭要靠女性來支撐,所以我畫了偉大的女性的架構來表彰。
洪根深,《形象》,墨、石膏、樹脂、畫布、壓克力顏料,145X112公分,1997
蔣:請您談一下1998年《情慾》。
洪:我來表達人的情慾。那個時候社會有同性戀,AIDS慢慢出現,對社會是一種衝擊,在《黑色情結之39》我用繃帶的形象,表達面目不在的軀體,AIDS帶原者沒有辦法面對的隔離、疏離。有一位去法國讀書的女詩人蘇士雅碩士論文是寫從洪根深作品裡看臺灣社會結構的轉變。
洪根深,《情慾》,墨、畫布、壓克力顏料,145X112公分,1998
洪根深,《黑色情結之39》,石膏、樹脂、紙、墨、畫布,91X116.5公分,1991
蔣:後期的作品中,您常常運用形體和周遭虛線線條。
洪:後來有些作品會走硬邊的線條,因為中國水墨的線條都很細,沒有比較寬的,應該可以跟硬邊結合,比如馬蒂斯借用中國的剪紙藝術發展出他的風格。後來我又用斷線,一個是不想再用以前的線條,第二個是我認為生命是一個伏流,如果這條線是生命現象,它有高峰有低潮,像一條河流一樣,潛藏地下之後到了某個地方又出來。在美術運用上,因為一個閉鎖的線條才產生出一個我們看得見的形體,如果我用斷續的線可以表達一個圓,那我何必要用實線來畫,而且更有想像空間,用虛的和實體產生對照,用簡單的跟繁複的對照處理。
洪根深,《自畫像》,墨、宣紙,68X68公分,2004
蔣:請您談談不同年代的自畫像。
洪:從早期到晚近陸續有自畫像,有的寫實、有的隱約、有的嘲諷,一種心理情愫的表白吧!比如《自畫像》(2004)有左下角我鍾愛的野百合花,右邊畫一双穿了二十年的鞋子、绷帶人偶,上面以漫畫的形式寫就「看人性反胃」。用自己的喜怒情愫表现自畫像,不同於一般的的自畫像。後來也會把文字加進去作品,因為中國水墨裡有落款,但不是畫面的一部分,那我想說把落款提升出來變成畫面的一部分,所以我把自己寫的新詩在這樣的結構中去處理。比如2003年《墨境》作品,傳統詩與新詩的合體,表白視網膜剝落開刀後的情境,這張作品捐給了「臺灣創價學會」。
洪根深,《墨境》,墨、石膏、樹脂、絹布、壓克力顏料、畫布,162X568公分,2003
蔣:2010年中有很多畫出來的方格,您在視覺上的思考是什麼?
洪:我每2到3年就會有些轉變,2007年我從旗山搬回來,一直想在符號上再有些變化。在西洋繪畫裡有錯視、歐普(Optical),這是一個,第二個是我要留白的空間,又不能完全留白,所以想說能不能用簡單的符號提升出來,所以我就打格子。2009年我開始用線畫格子再毛筆畫「」符號,利用光線打下來後的效果,呈現凹凸空間,變成一個視覺符號。如果我把Picasso《格爾尼卡》全部打格子後用自己的符號蓋過去,我要反問這張作品是我的還是畢卡索的,作品被改掉後產生伸縮和空間變化,這是我加上去的,如果我在後現代水墨用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會產生出一個作品歸屬的觀點和討論空間。
蔣:更接近您後來關於後現代的概念。
洪:對。
謝謝您今天接受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