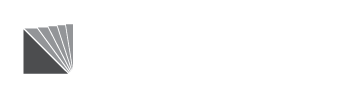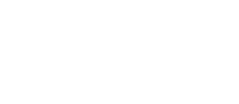「南台灣⋯⋯」
文/陳愷璜
0301992
若以〝南台灣〞為一命題來論述,則其名稱本身便已經清楚地標誌著數重與美學相關聯的內在意義:處在邊陲性地域與人文狀況孤立的邊緣性(une sorte de marginalite)(註):或者是內化過程(processus de l’intériorité)所外現(意識投射)的特殊氣質,這是藝術工作者主觀性意識作用後對藝術客體所進行的一種對話狀態(état de dialoguer) 。另一重奇妙的意義是客觀環境中的「氣候」使然,以「氣候」來論述,是因為從一特定空間條件中的情狀(ambiance)定空間條件中的情狀(afnbiance)所逐步凝鍊而成的精神氛圍(atmosphére),其最顯著的地方,莫過於台灣南部天空裡的清朗給人的一種形而下的生活解放,我將它稱為〝具融解性的流暢(la volubilité),這些自然天候的特殊條件,似乎與藝術創作中觀念之凝聚與主觀意識之投射沒有絕對直接的關聯性,卻潛在著主導創作者對待自我精神狀態的一種極為肯定的參照。如法國生命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在他著名的「物質與記憶(Matiére et Mémoire)一書序言中所敘述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他對回憶經驗以一種精神與物質之閭的交互作用的觀點來定義⋯⋯。」這種回憶經驗便是得之於生活內在的脈動與構成此脈動的諸物質元素。更深入的來論述這幾點:(當然,不以南台灣雙年展之參展者的各別作品來作為直接論述的基礎而代之以名稱──個無明確所指的文字概念來做為論述的依據,實有其深刻且必要的原因)。首先談到「邊緣性」,基本上,它意味著一種去中心論(décentralisme)的意涵,一種現代主義之後的人文自省狀況,所謂「核心」的神話被破除僅在單一性的均存在中而進行螺旋狀重新分的新狀態一成為多核心的樣態;同時也是當代世界性思潮的菁英主義之重組而成為分散的核心。影響它的主要客觀情況是一社會人文環境中有關被隱蔽而刻意曲扭的意識型態之蠢動與移位及社會整體結構的畸型變動──一種有意或無意對意識型態背離的人文景況;而與此交互作用的正是內在化外現間的一種〝類辯證關係〞的普遍萌芽,它斷然不是一種從屬的現象而是獨立產生的人文個性,也非〝游離〞一詞所能輕易描寫統括,概此〝類辯證關係〞存在於對諸客體象徵記號的〝純粹符號化〞與意識型態所主導的人文系統間之乖離,是記號與現實的辯證過程,是表層與深層的激烈鬥爭。(可參照黃宏德、陳榮發各有關的作品);(因缺乏自主的理論基礎所以我以〝類辯證關係〞名之。)創作者藉由主體的抽離而產生媒介性的對客體投射來達成此類辯證的活動;至於,內在化過程所指陳的並不是集體式的語言論述或觀念宣言,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為是根源於人與土地關係的一種意識性內在擬象(simulation),(可參照顏頂生作品),當然,這裡似乎存在著某種經驗論的吊詭之處一生活經驗;但若以一種語言學的角度而言,如結構主義思想先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言:「語言是一種先驗的結構,與人們日常講的言語是不同的⋯⋯」,(這就是結構與經驗現象之間的不同)。當然,也與現代藝術史上提出既成物(ready-made)觀念──杜象(Duchamp)的形象承繼(image-trouvé)有所不同,它是從〝無歷史必然性〞的生活環境中所湧現,是承繼生活感知性的形象創造。(參照葉竹盛、曾英棟作品),它也是這些〝邊緣性〞人與記號、造型、物體狀態對話的第一種活動姿態。(參照葉竹盛、黃宏德作品)。
其次,以天候的自然條件來隱喻並做為象徵藝術創作的情狀之擴張成為一種更為凝聚的團體性個體創作的氛團,更是符合了「南台灣」的地域及人文狀況尤其是社會條件;或者更具悖論(paradoxal)而且更深刻地來論述:「這種孤立意識係對質於環境中抽象化的二元論,人為地(意識型態地)使人和自然、個人與社會、思維與存在以及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的疑慮;在鋼鐵般的(隱喻南台灣的特殊經濟性工業結構及社會性結構中的勞動者)經濟關係支配下,此環境中的大多數人,只能是個消極旁觀者⋯⋯!或許因為在人的面前,存在著一種幽靈的東西,甚至存在著某種集體的抽象;但同時卻也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人儘管不是用具體的頭腦在思考,但總也在進行著思考;儘管不是以腳在移動,但也總是在移動⋯⋯」,而這也正是無法擺脫意識型態的變體作用──看不到人是社會的主體,看不到社會整體矛盾的根源,甚至還要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著它的「偽形」(pseudo-morphose)母體,自然地這種物化(la reification)意識只能產生扭曲的認識⋯⋯。(這種景況當然適用於台灣的每一個社會──如果以物化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必然地直接現實而言)。因此,它呈現在對材料處理的過程中之批判與對質可以鮮明地成為對人文的形上思辯(méta-critique),而這也正是〝南台灣〞所面臨無可避免的一種人文狀況與現實社會間的臨界狀態(état de 1’éritat critique)據此產生了一種無形而具體的反思──詮釋和意識型態可選擇在一個完全位於作品之內的領域起作用。
再者,談到無論以形而上、形而下、潛在地、心理地各種呈現方式的精神性寫照──〝具融解性的流暢〞;究其實質也無例外地處在與人文、社會諸客觀環節具悖論的地位上;因為這種〝具融解性的流暢〞係建立在一種具黏滯性(la viscosite)意識的內在質地中而具有它難以排解的矛盾狀態,是非立體性的被動狀態下所產生的主體投射之所與物;若以理想的狀況而言,此種流暢過程所衍生的符號代碼化(la codification)將是具普遍共相的傳譯;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有意識的主體不應被視為一個所與物和意義之源,而應被認可為諸文化力量和通過主體而起作用的諸社會代碼的共同產物。」這道出了〝南台灣〞潛藏而具困難度以致無法總體來實踐的一個客觀性缺憾;當然,這也是台灣環境普遍的另一具〝問題性〞難題。(可參照葉竹盛、黃宏德作品中的書寫,似乎對此能有所突破),更簡明地說,在無法克服客觀環境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試圖以另一個角度來探索,即此流暢的動作之源──身體;藝術家以造型語言做一切的作品,但無法以身體做;以造型語言隱藏的東西,卸由身體(活動姿態)說了出來。我們也可以參照巴特的另一段話來引證:「對於以往時代的任何一位作家而言,當他們都有一種從事前衛派創作的機會時,如果進行書寫的是身體,而不是意識型態的話──此處援引身體概念便暗示存在著一種超越作家思想的短暫文化特徵的自然基底,並企圖將自然置入超越文化條件和社會制度表面差別的人的身體之中。」那麼,這種具融解性的流暢之無法總體展現,將可以被意識性(觀念性)地克服;如此,試圖擁抱藝術宇宙的衝動將不難實踐。像法國觀念藝術家依夫‧克萊因(Yves Klein)的蹤身一躍一般,觀念化了構築宇宙的元素,同時也消隱在此宇宙之中,儘管它充滿了戲劇性,劫在時間中充滿了空間;在空間中凝聚了時間。而這正是我們期盼見到的純粹昇華。然而隱慝在此具融解性流暢的內面,似乎也同時存在著一種〝有教養的〞敏銳纖細(subtil),它並不是直陳式的,而以其引喚出來的抽象空間在進行著某種超過地域條件限制的與精神對話狀態──一種對藝術正面性(la frontalité)肯定而來的沈降成層(sédimendation),由痕跡、皺折、覆蓋、塗抹⋯⋯而生成的記號或符號,當然它的所處地域特殊性──〝重要的荒茫野性〞(1e capital sauvage),或許不可避免地有一種飄移的無法確定性。如塞‧湯布利(CY Twombly)作品中的某種情境般,他儘歸屬於在如何強調作品的游移、具體的猶豫不決之中。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也對他的作品如此的描述:「飄移朝向擱置的危機。」具危機的,不是方向,而是此種飄移精神上的突破。而這正涵容並緊束的關注著纖細與對知識的困愕,對童性稚拙的擬象,這些變形偏向的痕跡或符號已經不只是一雙〝美〞的手所能構建,而僅可能是他對無辜(innocence) 的不可能夢境之詮釋。(可參照黃宏德作品) 。或者,我們可以更簡潔明晰的給這樣的論述以哲學性的佐證,如柏格森所試圖瞭解並掌握的一般,他認為宇宙整體係被視為一單一的形象,從中試圖去瞭解對時間停滯的領略知覺;他分析記憶的時間性向度並記述著說:「瞬間的過去:以領會的同時,是感受(覺)(sensation)⋯⋯,是因為整體感受(覺) 詮釋了一種很長遠始基的擺盪之接續(la succession d’ ébranlement é1émentaire);至於瞬間的未來,在自我確定的同時,是一種活動的運動(action en mouvement),而我的現在(present),是同時兼具著感受(覺)與運動;因為我的現在形式成了一個絲毫未決的存在,而這運動將以活動來支撐並延續這種感受(覺)。」(可參照南台灣成員作品的普遍狀況。)
在今天因為殖民文化中意識型態無法擺脫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任何現代主義的傳統可言,(更遑論對台灣而言僅止於文字概念的後現代種種。)僅能擁抱,極度缺乏安全感地擁抱虛幻畸型的文化情結;正如對接踵而來世界人文思潮的嚴重誤解,這雙重的曲解使得人文境況益趨惡化,藝術家肩負了應該是超過藝術創作本身的教育效能,〝南台灣〞標誌的不是春風化雨,也不是藝術革命的前衛,卻是腳踏實地地對藝術以一種知性的致敬;如果藝術創作能超越社會意識型態的〝偽倫理〞,那麼現代主義的隙縫便可以超越彌平,並有望在現代主義之後的今天在藝術創作上達成一種純粹的、提昇的精神性領域擴張。那麼,藝術不是技術,藝術不是裝飾,便成為一個〝自明之理〞;更會是一種具絕對性意義的存在。如馬勒維奇(Malévitch)哲學觀一書中的(可供〝南台灣〞參照)幾個片斷,他在〝繪畫與感知性〞(peiture et perceptibilité)一章中提到:──思想(pensée):是激勵(或感動)的過程(或狀態)它在現實的或自然的活動中以一種觀點被展現。正因為如此,思想是某種東西,經由這種東西,它具可能性地對現象進行自省,也就是說瞭解、體認、領會、掌握意識、認知、確證以至建構;若思想不是激勵活動的一種過程,那麼它將是無法被識認的。──聚神凝視(contemplation)之抽象性攫取的或者不是以單純的想像或理由來完成;據此,理由(raison)甚至將成為更超然崇高而抽象的權力,感受性或想像在可能的尺度中,便可能足以抽象化偶然性混淆事物的實質(quiddité),並形式成了純粹絕對之(absolutos)自由狀態中普遍而特殊的觀念,這樣的聚神凝視在具自由性思慮的同時也是事物中對尋找自我沈思及巨大困頓的一種解放,在情感中,靈魂的深處將可以尋獲一種次序;如此,在屬於它自己的愛中,將有自由、解脫、純粹、具體與抽象。」
謹以此簡文來論述我所謂的〝南台灣⋯⋯〞。
註:在台灣特殊人文環境中,邊緣性意味著一種意識上的覺醒,與精神的核心,而不是一般文字概念上所指稱的〝游民〞。
資料來源:展覽畫冊。選錄自陳愷璜,〈「南台灣⋯⋯」〉,《1992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