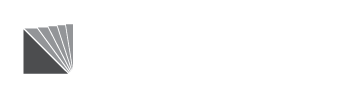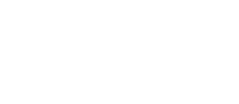雙城組曲.一闕寂寞──記南台灣新風格展的緣起緣落
文/ 蕭瓊瑞
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面臨解嚴前後特有的社會鬆動與精神解放;一九七○年代鄉土運動以來累積的文化自覺力量,也在這個時候具體而強烈地釋放了出來。為土地尋根、為歷史翻案,藝術界在社會的大脈動中,正展開一場激情而生動的展演活動;以往未曾有過的想法、以往不敢發表的言論、以往不可能採取的行動,都在這個時候,急遽地冒出頭來。社會的活力伴隨股市的活絡,台灣生命力的展現,宣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來臨。
激情的時代中,總有一些質疑自省的沉靜隱流。當藝術成為一種言說的工具、一種宣示的圖像,有人開始自省「藝術的本質」?這無關乎濁流與清流,卻毋寧是另一種策略的運用與選擇。
「南台灣新風格展」的推出,代表這股自省力量中較為顯著的聲音,而強調南方的特質,也標示著某種對文化「中心」與「邊陲」等既定思考的不滿。
一九八四年,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成立,原來服務於台北的黃宏德回到故鄉,進入這個新設立的文化機構服務。生活地點的選擇,多少已經呈顯某種生命特質的傾向。也正此同時,一些自國外留學歸來的藝術工作者,在台北人才飽合的情形下,開始集結高雄、台南兩地,以高雄新興都會的經濟實力,結合台南古都特有的文化風情,操持不同於台北藝壇的運作方式,凝塑出一種放牧與隱逸夾雜的特殊人文氣質。
高雄現代畫學會,那種簽名在裸露上身,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生猛活力,在台南則對比著一種孤高、疏離、安靜、隱逸的「南朝氣息」。雙城間原有頗為不同的文化樣貌,但當他們面對「台北中心」的壓力時,卻極其自然的結合在一塊,尤其他們那種不屑於汲汲投身名利戰場,對假冒偽善者也有著一份與生俱來的深痛惡絕之感,同時相對地,他們卻也不甘於被完全埋沒;因此,他們偶爾聚集、放論時事,對藝術與生活採取若即若離的姿勢。
一九八六年,是解嚴的前一年,「南台灣新風格展」正式在台南文化中心推出首展。參展者有高雄方面的洪根深、楊文霓、葉竹盛、陳榮發、張青峰,和台南方面的黃宏德、曾英棟、顏頂生、林鴻文等九人。他們之間,最年長的是四十歲的洪、楊、葉等三人[ 1946年生] ,最年輕者為二十五歲的林鴻文[1961年生] 。
這個組合的特色,一如其初始命名──「南台灣新藝術‧風格展」,一方面標舉了地域上的自我認定,二方面則在強調「新藝術的堅持與追求,而「風格」的呈現,則是主要的手法與目標。這些思想,具體表白在一篇由葉竹盛執筆的類似宣言中[註1]。
這篇文章,文字相當生硬,但可以看出他們對「沉默的南台灣,流行著三、四十年代由日本移植而來的印象派、野獸派等毫無創見的二手貨」之現象,深感不滿;因此,他們主張藝術家應積極面對時代的變動,選擇適當的創作材料與繪畫語言,來呈顯自己的「藝術觀」。
事實上,第一屆「南台灣新藝術,風格展」的作品,除洪根深與楊文霓、張青峰三人的作品呈顯較穩定而成熟的風格外,其餘數人,均帶有強烈的實驗與探索的意味;作品的不成熟,一如那篇文字生硬拗口的宣言,頗有眼高手低、力不從心的感覺。而有趣的是:這幾位風格未見成熟的成員,日後反而發展出頗為雷同的藝術走向,成為所謂「南台灣新風格展」的典型代表;而在首展中,作品已趨成熟且具一定份量的洪、楊、張等人,則先後因不同因素,脫離畫會。
洪根深,與楊文霓、葉竹盛同齡,但就輩份論,他是南台灣,尤其是高雄地區現代繪畫的老前輩。在七○年代的現代水墨風潮餘波中,洪根深結合劉國松等人抽象水墨與何懷碩造境式水墨的風格於一爐,頗受畫壇注目與肯定;之後,長期經營自我風格、關懷社會變遷與文化整建,也戮力推動南台灣的現代繪畫運動。一九八六年「南台灣新藝術,風格展」的成員,他受邀參展,也是基於支持現代藝術的一貫理念。在首屆展覽中,他以裝置的手法,將一些時裝模特兒模型,纏滿繃帶,在投射燈仰角照射下,呈顯出他當時對人性與生命思考的關懷;這種風格,事實上與他在水墨表現土的繃帶系列,是頗為一致的,然而放在整個會場中,卻顯得格格不入。在前揭葉竹盛的宣言文字中,雖然多處流露出對環境變遷、科技進步、社會問題、經濟危機的關懷,也強調要用多媒材的手法透視、呈現時代的大背景。然而在實際的表現土,除了洪根深的作品有直接的觸及外,其餘多是在材質與形式上,進行純粹的造型與探索。此一差異,在第二屆的展覽結束後,更形突顯,洪根深體諒畫會成員對於的「會場整體風格」考量,乃主動退出。
至於楊文霓,是知名的陶藝家,尤其在一九八○年代之後,以其留美學習現代陶藝的經歷,對南合灣現代陶藝的啟蒙,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楊氏的參與南台灣新風格展,固然由於其作品呈顯出來的高度純淨、簡逸特質,與其他成員作品,頗有相融之妙;但本質上,這種相融相通的現象,實緣於陶土造型與釉色變化本身的媒材特質,而不完全是楊氏本人的思想傾向有以致之。一九八八年的展出,是南台灣新風格展極重要而具代表性的一次展出,楊氏在創作自述中,云: 「對我來說,器皿是有個洞,你可以看到裡面,而它亦可以裝載,假如它是有味道的陶瓷,那麼多少它會帶有一些空間感和雕塑的份量;而它原有的實用性,並不會與我想要做的有什麼衝突。
目前我的作品,仍然是這幾年來欲想探討一個中心問題的延續,以作陶的觀點來處理空間和平面的問題,在我的願望裡,它們不是二個平行或矛盾的因素,而是會交錯涵接而為一,而這器皿的生動和精神,決定在我所使用的方法和安排的過程。」[註2]
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呈顯楊氏所關心者,仍是藝術造型本身的問題,陶藝之於楊氏,乃是一種界於雕塑與繪畫之間的微妙媒材,既是立體又是平面。這種強調純粹形式的傾向,固然有相通於南台灣風格展中其他成員的部份,但在創作的態度上,楊氏卻與其他成員頗有差異的,如果說:在「道」「象」二者之間,楊氏係屬「先象而後道」的類型,新風格展的其他成員,則屬「先道而後象」的類型;換句話說,前者屬「形式先行」,後者屬「意念先行」。這種本質上的不同,終至使楊氏與新風格展越行越遠,在一九九○年的展出結束後,也不再參展。
張青峰在許多方面,事實上都與南台灣新風格展的成員有所不同。他一九五四年生於雲林,和其他以高雄、台南兩地為出生的成員,顯然「南台灣」的氣息少了許多,而台灣師大美術系畢業後,留學紐約州立大學,其作品雖亦強調材質的特色,但擁有強烈的造型性,尤其充滿理性的思考。事實上,張氏是一九五○年代前期出生的年齡層中,相當具有大氣魄與大師風範的傑出藝術家;其首展中的一件作品,取名「開,和」[似乎如為「開,合」更為恰當],以折疊如扇面的長條木片,排列成一個直徑約五百公分的大圓形,此圓形置於牆面與地板之間,形成一個半圓直立、半圓橫臥的造形,隨著觀者立足點的移動,折疊的木片,本身既產生光影、角度的視覺變化,直立的半圓與橫臥的半圓間,也隨著會有一種「開」、「合」的意象變化,近觀則如大圓,遠觀則如半圓,大圓似合,但視界為開,半圓似開,但視界壓縮,又如雙唇的密合。一九八八年的展出,除平面的抽象繪畫,以多媒材[主要為壓克力顏料、石墨、粉彩,而無自然物或現成物] 強調畫面的造型性外,主要引人注目者,仍是幾件立體的作品。一件取名「結局」者,以一塊偌大的畫布[長寬約有240×220公分];用六條繩子綁成六個角,並拉開,猶如一張剝開的牛皮,表面以青藍、紅紫等絹印色料揮灑得相當濃稠,然後在中間以刀片劃開,露出底下的白色襯布,這種綁、拉、割、甩的強烈意象,配合「結局」的題名,予人以一種生命掙扎的聯想,猶如觀賞史丁的畫作一般;但張青峰的作品,手法乾淨俐落、節制而非狂亂,理性分析多於率性發洩。另一件「生界」,亦頗為別緻;將一塊圓木切成四分之一,放置在一個張開的紙製購物袋上,上重下輕,產生一種視覺的緊張,與心理的壓力,唯恐購物袋會隨時被壓扁; 由於木頭和紙袋原本是同一材質,都是樹木的殘體或再製品,再加上藝術家把木頭切割得寬度和紙袋大小完全一致,讓人產生既合體又相斥的微妙心理,大有「煮豆燃豆箕」的味道,作者將作品的英文名稱取作「The four miseries」,意為「四不幸」,頗有佛家的生命體悟;「生界」即為「四不幸」。這種對材質的運用,這種對生命或生活的反思,或許是促使張青峰和南台灣新風格展成員結合在一起的主要特質; 但在創作的手法和態度上,他們其實有著迥然不同的方向,張氏或許更像一個理智的科學家,透過自然真理的發掘,而體悟人生,其他的成員則似浪漫的哲學家、隱士,以不著痕跡、不假虛飾的態度,傾吐胸中逸氣。張青峰一九八八年以後的遠離新風格展,其因素應不止是由於工作地點的北移一端。
一九九二年的展出,是新風格展風格確立的一年,當年展出因曾英棟出國,而使參展成員只剩葉竹盛、陳榮發、顏頂生、黃宏德、林鴻文等五人,這種情形,事實上,實更合乎新風格展真正的性格與特質。其原因在:即使曾英棟自始迄今持續參與新風格展的展出,但本質上,曾英棟與其他幾位成員間,仍有諸多氣質與手法上的根本差異。曾英棟那些以貝殼、熱帶魚、變色龍、石龍子,和天堂鳥等符號構成的作品,充滿了視覺感官上的炫麗色彩,直覺多於思考,裝飾多於造型;基本上,這是偏向美洲的文化傾向,而不同於其他成員之偏屬歐洲系統的思考。曾英棟的作品毋寧更讓人聯想起同是師大畢業的許自貴。
如果再剔除曾英棟,那麼所剩下的新風格展中的幾位成員,全屬藝專,[今台灣藝術學院] 系統,也就不讓人覺得意外了!在戰後台灣的美術發展上,從教育的系統觀,大抵有師範[含師大和早期師專] 、文化、藝專三個系統;如果範圍再擴大些,還可以加入政戰一系。這些不同的學院系統,由於學院教育本身的取向,再加上學生畢業後的出路不同,往往呈顯出各具特色的創作走向。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學生,畢業後有著從事教職的生活保障,走向深化學院傳統,或在紮實的「基本工夫」中尋求「現代」的表現,是普遍的特色;文化大學美術系的畢業生,少數進入教職,多數在專業美術家的路徑上掙扎,於是帶著一份反社會、反傳統的精神,便成為他們頗為一致的特色;激烈者,直接進行強烈的社會批判,消極者,則走向一種文人式的疏離與隔絕。至於藝專畢業的學生,他們之中,頗多具有設計方面的專才,對純粹形式的探求、媒材的開發,尤具一種他校所無的傳統與興趣;而留學西班牙、義大利等地,又成為學長學弟間長期相互牽引的一種鎖鏈,即使未出國留學者,也在這種傳統感染中,表現出頗為類同的藝術走向。
藝專校友此一系統的源頭,可以清楚追溯到西班牙戰後成名的「不定型畫派」大師安東尼‧達比埃[Antonio Tapies]。他早期的畫風,接近同為西班牙畫家米羅的風格,有超現實主義的傾向;之後,由於兩次大戰帶給人類巨大的心靈創傷,他開始轉向一種厚塗的技法,排斥一切有關具象的記號及自然物象,刻劃出傷痕一般的洞穴和線條,由材料來決定形式,由形式而衍生情感。這種強調肌理、質感的畫面,深深切合西班牙那些古老而浪漫的傳統建築與風情,也對具有禪學或老莊思想的東方藝術家,產生特殊的魅力與啟發。台灣最早受其影響者,為一九五六年留學西班牙的蕭勤[註3];而在數十年後,則再度影響到一些相繼留學西班牙的藝專畢業生。
葉竹盛即謂:「記得在西班牙,旅行時常拍攝自然留來的痕跡如牆、門、窗及有觸心的物質,雖然非常喜愛,可是沒有很明顯在作品中出現。而到現在,以前所留的意象才和創作結合。」[註4]
陳榮發也描述他在西班牙留學時創作的一件作品說:「『冷‧碑』─作品是在異鄉之實驗性作品之一,它是具象的,亦同是抽象的。由渲染、撕紙、裱貼、密雜的撞擊筆觸、乾枯的橄欖樹枝,以及具有質樸感之土黃色牛皮紙所構成,所呈現的是苦難、衰敗、孤獨而淒清的憂鬱氣氛。是由電影『沙戮戰場』所帶來的震憾以及思鄉之情所激發的情感渲洩之作。」[註5]
不過這一系列的作品,在台灣的真正形成風潮,則與一九八二年的林壽宇回台有關。林壽宇在一九七○年代,即以Richard Lin的名姓,在歐洲抽象畫壇擁有一席之地。這位故鄉台中的世家子弟,早年留學英國學習建築,之後轉入藝術創作;其自馬勒維奇幾何抽象出發的絕對主義風格,隨著回國展出,為台灣鄉土連動以來陷於低潮的現代繪畫運動,注入一股新鮮活力,迅速吸引一批年輕人追隨左右。一九八四年在春之藝廊的「異度空間展」,正是他和學生聯合推出的一項大型展出。除後來活躍北部的莊普、陳幸婉、張永村,和中部的程延平外,同時參展的葉竹盛則因故鄉高雄的原因,與一九八五年獲得雄獅新人獎的黃宏德,聯手推動「南台灣新藝術,風格展」的成立。
首屆的「新風格展」成員,除前提洪根深、楊文霓、張青峰外,均可明顯見到林壽宇絕對主義或低限主義、材質主義的交錯影響。即使日後最具發展潛力與實質成績的顏頂生,仍在首屆展出中,表現著一種畫面分割與極簡筆觸的淡逸風格。黃宏德、林鴻文等也都是在極簡的畫面中,以一種飛鴻留爪的不經意筆觸,捕捉著一種經意的效果。倒是留學西班牙的葉竹盛和陳榮發,藉著材質的排比,散發著較強烈的質感和色彩。
就在新風格展推出首展的同一年[1986] ,《雄獅美術》也在三月號推出「戴壁吟專輯」,這位留學西班牙與達比埃有著直接情誼的藝專校友,和葉竹盛同齡[1946年生] ,其因應一九七○年代中期能源危機而研發自製紙和混合媒材所創造出來的特殊風格,引起台灣畫壇極大的興趣,同時似乎也對新風格展的其他學弟,產生了直接、間接的感召和啟發。
戴壁吟背後源頭的達比埃系統,就形式言,似與林壽宇源於馬勒維奇幾何抽象帶回來的絕對主義,有所矛盾,但強調材質本身的精神性,卻是一致的;東方哲學中無為、靜諡的思想,也成為他們積極汲取的精神泉源。新風格展的成員就在這林壽宇與戴壁吟的兩種極端型式中,自行轉化,走入一個禪思與疏離的純淨、簡淡風格中。
就新風格展的團體活動言,一九九二年的成熟,也是畫會瓦解的開始。各個成員在九○年代前期逐漸以同中有異的風格,坐擁一片天,甚至成為,北台灣畫廊、美術館垂青眷愛的對象;而一九九四年的展覽,已經是由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新新人類」擔綱;新風格的成員,作品才剛成熟,已準備退出幕後,進行「發掘新生代」的使命,扮演前輩的角色了。
九四年的新人展結束後,原已成為雙年展定制的展出,並未如期推出後續行動;九七年的展出,與其說是畫會成員的再度凝聚,不如說是文化中心工作人員的勉強撮合。緣起緣落,「南台灣新風格展」似乎也如八○年代中期興起的台灣南北各現代藝術團體一樣,正在走入歷史,即將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詞。
但這樣的發展,並非是全然悲觀的,南台灣新風格展的緣起緣落間,事實土也成就了成員各自殊異而值得繼續開發的個人風格。如葉竹盛一九八八年被作為畫展封面的作品,以稻草、石膏、壓克力、鉛筆,造成的一種燃燒與餘燼的強烈意象,即予人以極深刻印象; 相信光就這件作品,已足以成為南台灣新風格展為台灣美術留下的一個美麗標點。
至於黃宏德以毛筆沾墨,一筆成道、落墨成象的禪思,或將自己陷入一種可畫可不畫的困境之中,看了他的作品,讓我們想起東方畫會的李元佳。但對以生命獻給藝術的人,即使他不再執筆,我們仍將懷念他。
林鴻文的心象風景,事實上仍多取材於現實的一角,「紅城心式」[註6 ] ,近幾年來,對古都地方文化事務的積極參與,已使其作品,逐漸脫離個人內心獨白的形式,而在色彩、造形上有了更大的開闊,尤其一九九七的作品,明顯可以期待一個新的創作高潮的來臨。
倒是陳榮發那些飽含悲壯情緒的作品,多年來,成為南台灣最濁重有力的一把號手,對這位大器晚成的藝術家,我們期待他持續保持宏聲的嗓門,不要轉為優雅的小調。
倒是顏頂生,從他的種子系列開始,便背負著畫壇最大的期待,似乎同時代的抽象畫家中,沒有人能比他更深切的植根於黃色土壤中。歷經一些曲折,他現在回到台南將軍的故鄉,親自下田,種植果樹;這樣真實的生活經歷,必將為顏氏帶來更紮實的創作源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不改。」[老子25章]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老子21章]
南台灣的雙城,在二十世紀末的大時代變局中,因緣際會,合奏一曲寂寞短歌,有來自遙遠西方的啟蒙,有漫漫傳統的滋養,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去印證那惟恍惟惚的「真理」。
南台灣新風格展的是否持續展出,已成為無關緊要的形式;關心藝壇發展的人士,更關懷的是:這些在台灣歷史脈動中浮現的藝術工作者,不管當年是出自策略性的選擇,抑或心性的自然抒發,他們以青春生命換得的作品風貌,是否可以在生活的困頓或職業的安逸中,持續保持自發性的發展與延續?而我們除卻急急冠以圖騰式的標籤外,可否給予這些誠心而嚴肅的創作者,更多的關懷與支持?
[本文旨在對南台灣新風格展的生發本質,進行一種歷史的檢驗與澄清,至於對主要成員作品的深入論述,則有待另外專文的探討。]
註釋:
註1:參見【1986南台灣新藝術。風格展】展出目錄,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86,台南。
註2:參見【88”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作者自述,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88,台南。
註3:參見蕭瓊瑞【宇宙過客─蕭勤的心靈逆旅】,【蕭勤】,帝門基金會,1996,台北。
註4:葉竹盛【我的語言─素材】,【1990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0,台南。
註5 :陳榮發【時空交錯的點】,上揭【1990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
註6 :【紅城心式】為林鴻文1994年於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展覽之名稱。
資料來源:展覽畫冊。選錄自蕭瓊瑞,〈雙城組曲.一闕寂寞——記南台灣新風格展的緣起緣落〉,《1997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6-11。